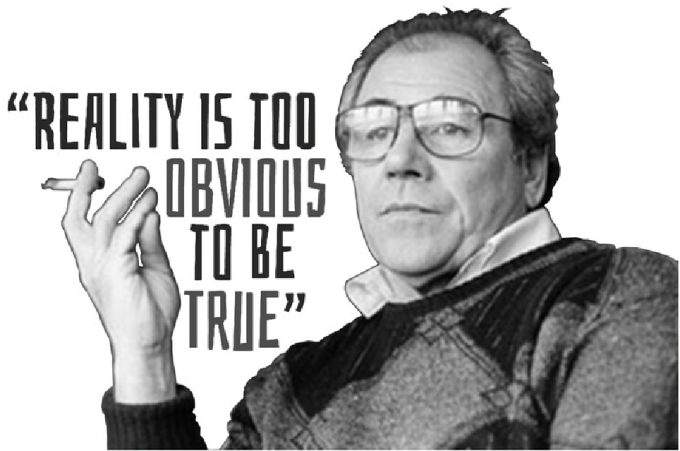永无止境的日常与被取消的超越性
”故事“的退却已经成为时代浪潮。或者说,整个动画界正在失去其 “讲故事的意愿”。也许这是过去几年的趋势,但无论在电影或是电视剧中,”叙事性”似乎已经急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描绘“日常”的风潮。描绘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妙情绪——或者说,更直接地描绘他们的 “氛围”的作品显然在增加。这不再只是一种趋势,甚至给人的印象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流派。戏剧性的情节不再像以往一样受到追捧。
——押井守(著名导演,动画制作者,代表作《攻壳机动队》)
在如今的动漫文学创作中,对于日常的琐碎描写开始变得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类被称之为“日常系/空气系”的作品——在其中并无明晰的主线,即便是描绘校园生活也并不像过去那样有围绕着“全国大赛”这样的目标而竞赛奋斗的剧情,即使有男女主/家人的存在也回避对于爱情/亲情的描写(甚至可以全为同性主角),因为爱情和亲情会毫无疑问的成为“故事”的要素。在过去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也不乏对于平凡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写,但日常系/空气系作品对于现实的描绘刻画俨然已经超过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是对于现实的批判并指向在此之上的超越性,而在日常系/空气系作品中却并不指向任何意义上的超越性。本文试图通过对日常系作品的探源,展现出当前世代的精神图谱。
过家家?催眠?日常系作品究竟魅力何在?
在对日常系作品的粉丝访谈中,一位粉丝这样自嘲:“虽然知道就是一群小女孩在一起过家家,但只要看着就感觉很满足了。”而当被问及日常系作品常常被诟病的“毫无剧情”“催眠”等问题,一部分粉丝认为并不存在这种问题,这类作品同样能够引人入胜,而另一部分粉丝则认为“催眠”恰恰意味着这类作品能够在忙碌的一天后给予自己内心的平静,能够看着少女们百无聊赖的日常入眠也不失为一种惬意的体验。
这一回应或许是令人咋舌的,在传统意义上,“催眠”对于任何一部商业作品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催眠”意味着叙事的缺乏,冲突矛盾的缺乏,这对于传统的故事叙述者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而当被问到日常系作品究竟在什么地方吸引到自己时,大部分受访者都给出了如下的答案“可爱的人物”“人性的温暖”“有共鸣”,这些回答听起来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或许对于这些日常系作品的粉丝来说也很难说个明白,总结来说都归结为一个暧昧的词——治愈/救赎。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日常”的历史
什么是“日常”?对于这个问题最简单的一个答案或许大家心中都有数,“日常”是我们每天的吃饭睡觉,两点一线,机械重复,同时“日常”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日常生活区别于历史书中的纵横捭阖跌宕起伏,常常意味着琐碎与平庸。日常是那么普通而又熟悉,但事实上“日常”这个概念进入文学与哲学的视野,也只是晚近的事情。在古希腊的史诗戏剧和圣经中的神话故事中,并不存在日常,各种英雄身上的勇武与智慧都与普通人的日常相去甚远。即使是在中国文学的田园生活中,所表达的也往往只是一种消极避世的否定意味。乃是在西方市民阶层兴起后,文学才第一次自觉地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世俗精神以及其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一度引领时代的潮流,英雄传奇开始让位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小说的兴起》这部论著中英国理论家伊恩·P.瓦特这样分析,在现实主义把视点移到日常生活内部之后,小说中的人物开始如同生活之中一样有名有姓,具有独特的性格,而且所有的故事都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总之,一切都细致得栩栩如生,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这也是阅读之中真实感的来源。但现实主义对于日常生活的注目并非意味着记流水账、对叙事的舍弃,老舍通过对人力车夫祥子不幸遭遇的冷峻描写揭露出旧社会不给人活路的事实;斯托夫人通过对黑人汤姆叔叔境况的诉说间接引发了一场反对黑人奴隶制度的社会变革。现实主义的文学通过对于日常的细致描绘实现对日常的批判,从而指向某种超越性。
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感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感,需要注意的是,现实并不等同与真实,在心理层面上,人总是倾向于将现实当成真实(抑或是真实得以被追寻的地方)。古德曼将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解读为同构的关系,古德曼并不将日常生活世界与文学艺术世界的差别视为虚构与实在的对立,现实世界和文学艺术世界同样是由符号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二者并无本质区别,而文学艺术本身也并无独享的符号系统,如文学文本中的符号同样会在非文学文本中出现。那么为什么会有现实世界与文学艺术世界的分别呢?在现实世界的认识活动中的符号建构是与指谓相交织的,并且其符号建构总是受到指谓行为的制约,受到被指涉对象的校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主观性的入侵,这其中构造与指涉的交融使得符号早已融入日常(符号被日常生活所“同化”“吸收”),符号成为了“真实”本身。而在审美活动中,人积极投身于活跃的符号创造,并沉醉于创造的愉悦之中,他并不将眼前创造的形象指认为真实,中断了指谓现实世界的行为,从而诞生了超越的可能。
但在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中,由于符号、影响的病毒性增殖,其与“原本”的联系就此失去,其对于现实的指涉功能也随之消失,符号与符号之间相互交换,且这种交换是以符号不再与真实交换为条件而达成的。符号难以与日常相融合,而是保持着一种间距,这就抗拒了日常对于符号的同化,而得以获得了自我建构的力量。而随着不断增殖的影像将日常生活世界覆盖,现实也成为了“超现实”。过往区分现实世界与文学艺术世界的界限消解了,现代社会成为了居伊·德波所说的,日常审美化的“景观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对于现实的描绘,也不过只是对于“虚拟”“影像”“仿真”的描绘,甚至于有学者这样感慨:“由于今天的现实本身已被虚拟化了,艺术只有不再虚拟才能发挥它的救赎功能。 ……今天的艺术将以展示那个不能被虚拟的存有领域对抗全面的审美化进程,来拯救人们那业已被审美化所操控或麻痹的感性。“
作为日常系作品所指涉的“日常”的历史
作为日常系作品和动漫文化诞生的日本,在战后虽历经冷战铁幕、共运学潮,最后却也是在消费社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并到达了九十年代泡沫破灭的十字路口。对于左翼革命与核战争的幻想与畏惧始终笼罩着这片大地,但结果是政治革命没有来,核战争也没有来。在1988年大友克洋导演的名作《AKIRA》中,建立在现代科技之上的东京的钢铁丛林中,有的是反帝游行的革命者,有的是追逐神临拯救世界的新兴宗教,也有不知生存意义而终日飙车暴走的少年。也是在1988年,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作了名为“历史的终点”的报告。
对于泡沫破裂前夕的八十年代后半,提出“御宅族”名称的中森明夫这样写到:“然后有一天,导弹真的会拖着红色的尾巴飞过我们的上空。到那一刻大概神明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是的,终焉之时就是如此突然。……世界末日那一天,我们大概还会在售票处预订下个月芝浦Inkstick的门票吧。世界末日那一天,我们大概还会在日历上标记大减价的第一天吧。世界末日那一天,我们啊,大概会好好地把鞋带从阿迪达斯上取下来吧。”对于导弹飞过的恐惧与平淡的日常是80年代日本消费社会的两面,一面是核战争背后宏大叙事仍有影响的实感,一面是泡沫繁荣下“永无止境的日常”——这个词来源于社会学家宫台真司对于八十年代的分析,他用于形容八十年代流行于少女中的思潮:“生活不会有大的进展,也不会有可怕的毁灭。如同《宇宙战舰大和号》那样的崇高意义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这样,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像在学校一样地,以戏谑的态度度过每一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描绘搞笑日常的《福星小子》应运而生,成为划时代的作品。但泡沫繁荣在诞生”动物化”的消费享受的同时,也孕育出对无尽日常的畏惧——乌托邦同时也是反乌托邦:不受欢迎的人永远都不受欢迎,无趣的人永远都无趣,被欺负的孩子永远都被欺负。作为对80年代前半日常剧的反动,各种对于末日审判,最终决战的幻想甚嚣尘上,一些人开始寄托于某些外部性的力量来将日常终结或是消费虚构的自我实现。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核战争的幻想开始远去,但这股思潮的结果是1988-1995年间震惊世界的奥姆真理教事件。
宣告80年代终结的不只有红旗的落下,还有同年破灭的泡沫。如果说80年代还是对于社会价值实现不确定性的思考,90年代要面对的是社会价值实现的不可能性的接受。既不可能在这个废墟般的世界中实现些什么,也无法渴求怎样的外部性来将其终结,作家鹤间济这样写到:”二十二世纪一定会来(当然,二十一世纪也即将来临,因为不会有所谓的世界大战)。世界绝对不会走向终结。和‘异界’和‘外部’接触是满足不了的。还是想要更大一些的刺激,要是真的想要终结世界的话,最好还是去做‘那件事情’。“这里的”那件事情“,指的就是自杀。死亡好像成为了这永无止境日常的唯一”外部性“,文学作品试图去描绘死亡以获取这一“外部性”,但到底来,死亡也仅仅是作为符号而被消费,并在数据库般的生产消费中成为仿真。这一时期内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对于性爱死亡的关注——心理剧/精神分析疗法的盛行,由于社会性实现的不能,人们只得转向内在的精神创伤以获得个人实存之确证,典型代表是被东浩纪等后现代宅文化研究者视作划时代的EVA(新世纪福音战士),其时常被人称道的最后几集的意识流剪辑与“人类补完计画”的结尾,并非是通过主人公自身的行动(遵从父亲的指示,就像七八十年代《机动战士高达》中的阿姆罗一样义无反顾的选择驾驶巨型机器人与邪恶力量(他者)作战),而是不断的回避,拒绝父亲对他的要求,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想获得父亲的承认,但结果是虽然他按照着父亲的要求去驾驶eva对抗被称为使徒的邪恶力量,却不得不将朋友与唯一理解自己的人(使徒之一)杀死。为了获得父亲(社会)的承认,而去与敌人(他者)战斗的结果是被一次又一次的伤害,这是九十年代日本社会性实现低下的表现,但动画构想了一个名为“人类补完计画”的结局,通过宗教神秘学式的结构与母性的隐喻让所有的人们都在精神分析式疗法的拷问中消解了AT立场(动画中对人与人间隔阂的隐喻),并在一个所有人获得相互理解的世界中迎来结局。这之后便开启了被东浩纪称之为“世界系”的文脉——在抽离了社会(父亲)的世界中,背负世界命运的女主(对于世界的母系想象)拯救(认可)弱小无能(社会性“不能”)的男主的故事。
但事实是,在90年代社会性实现低下的社会中,或许不与他人/社会接触,封闭自己的内心可以不让自己受到伤害,但这样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人只要活在世界上,就注定要和这个社会,与他者产生联系,或许可以选择回避,但终究是会在某些决定性的瞬间与结构相遇,而在现实中也不存在会来拯救自己的“少女”,宇野常宽认为所谓“世界系”的文脉只不过是带有女性歧视的幻想(畏惧他者/父亲而转向自我承认/母亲),结果也确实如他所说,世界系的风潮在两千年左右就告于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零零年代的决断主义——当今层出不穷的互联网亚文化圈子混战就是其一例证,“小粉红”“网络左派”同过去的人们一样一遍遍喊着爱国主义/左翼的口号,但他们当真和旧有观念中的左派一样吗?并不是,他们的行为大多只是停留在一遍遍复读断章取义的经典与无穷无尽的网络辩论,如果现实与既有观念不符,也只会认同符合自己观念的现实,大家说着共同的语言却无法理解,所谓的爱国主义/左派理想也不过是作为构建网络共同体想象的亚文化罢了。宇野常宽认为,这是对于后现代状况的无意识应对,虽然存在对于社会性实现的怀疑/不能,但我们仍然需要心理层面上生存的意义,虽然明知毫无根据,但仍然要选择相信这个相信那个(小叙事)(心理层面而非实践层面),以左/右,又或是世界系式的浪漫主义来生成围绕自己的封闭空间,即便什么都不选择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决断,这就是被宇野常宽称之为零零年代想象力的决断主义。
日常中有救赎存在吗?
探寻完“日常”与“日常系”之前的历史,让我们回到日常系作品本身,这种舍弃了故事性本身的作品如何得以提供救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如何得以有生命力,正是因为人们需要叙事的结构,在“意义”的层面上理解世界,拒绝日常世界(尤其是苦难)的无意义。但在宏大叙事日渐消退的后现代,在日常审美化真实成为超真实的消费社会,在社会性实现开始被怀疑的现在,宏大叙事的一致连续变得不再可能,现实社会变得不再透明(难以以叙事的结构来理解、预测),人应当如何来生存,如何获取生命的意义?90年代后半的心理剧的衰退已经证明了完全拒绝外部叙事的不可行,于是在00年代转向了所谓的决断主义,变成了如宇野常宽所说的无数小叙事的大逃杀,而这其中诞生了“日常系”这样几乎无故事性的类型作品,并非以叙事的结构来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而是对理想化日常生活本身的刻画,它并不描绘比赛的胜利,也不是与我们崇拜的人在一起,而只是在回家的路上的小憩与房间里的交谈,在其中,消费者发掘了一种理想化的“青春”观念。这些男性消费者所寻求的是一个充满社会性的理想化的空间。换句话说,并不是从青春中所得到的某些东西,而是青春本身,比如社团活动以及与朋友共度的时光,成为了描绘青春的目的。在现实的日常之中,我们的感觉是闭塞的、痛苦的、无法呼吸的,而这样对于日常的拟像,成为了我们的理想的、想要经历的、并非日常的日常。或许追随东浩纪的那些作者们会把其称之为“二次元存在主义”,并不用走到外部世界之中,而是在“游戏”之内,将“一瞬间”当作现实予以肯定。我想,这未免对于日常生活的萌要素消费进行了过于理想化的想象,不是将理论付诸实践,而是继续沉浸于决断主义的角色扮演和拟像的消费,仍然只是对于现实的逃避,是不可能获得所谓的“救赎”的。
参考文献
南帆. 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J]. 当代作家评论,2012(5):28-36.
马大康. 古德曼:日常生活世界与文学艺术世界[J].学术论坛,2015,38(04):91-98.DOI:10.16524/j.45-1002.2015.04.002.
彭峰.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F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中森明夫.東京トンガリキッズ,2004.
宮台真司.终わりなき日常を生きろオウム完全克服マニュアル,1995.
鶴見済.完全自殺マニュアル,1993.
宇野常寛.ゼロ年代の想像力,2011.
宇野常寛.リトル・ピープルの時代,2011.
東浩紀.ゲーム的リアリズムの誕生~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2,2007